
存款数字的飙升并非繁荣的信号,而是经济转型期的焦虑体现。 央行数据显示,中国M2货币总量已突破335万亿,远超GDP两倍的合理水平。 多出的65万亿资金淤积在银行系统,无法进入实体经济。 这种“血管堵塞”直接导致消费市场乏力,企业投资收缩,就业市场承压。
房地产曾是家庭财富的“压舱石”,占比高达60?0%。 但如今房价下行,一线城市平均跌幅达30?0%,北京跌回2016年水平,深圳甚至退至2015年。 家庭资产缩水后,“留足现金应急”成为理性选择。 年轻人面对就业压力和收入不稳,连结婚生子都谨慎,进一步抑制消费信心。
这种保守心态与过去形成尖锐对比。 父母一代享受分房和铁饭碗,如今家庭投入几十万培养的大学生,月薪三四千成为常态。 消费信心的缺失,直接指向房地产熄火后的连锁反应。买房带动的钢铁、水泥、装修、家电等产业链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,社区餐饮、商超纷纷关门。

房地产失速背后,是中国经济“三大法宝”变为“三大挑战”:人口红利消退、全球化遇阻、土地财政难以为继。 1962-1976年婴儿潮群体逐渐退休,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786万暴跌至2024年的954万,总生育率1.1甚至低于日本。 同时,WTO带来的“世界工厂”优势受关税壁垒冲击,订单向越南、印度转移。 城镇住房套户比已达1.09,房子够住了,人口却减少了。
破局方向已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:科技创新当头、内需市场做引擎、深化改革释放红利。 国家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每年投入1万亿支持科技,AI大模型研发成本仅为美国的1/10,机器人专利占全球2/3。 新能源车出口量全球第一,5G基站占全球60%以上。 人才红利取代人口红利,每年1000万毕业生和近2000万工程师构成全球最大高素质劳动力池。

内需市场潜力巨大。 中国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服务消费占比仅46%,远低于美国的68%。 老龄化催生的医疗养老、消费升级带动的文旅教育,都是万亿级蓝海。 政策端通过2000亿设备更新贷款、消费品以旧换新覆盖3700万人、生育补贴全国铺开,试图解决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后顾之忧,让老百姓敢花钱。
要让沉淀的161万亿存款流动起来,关键在于打通资金梗阻。 5年期LPR大幅下调25个基点,多地中小银行密集降存款利率,正是为了引导资金从银行流向市场。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经验表明,短期阵痛往往换来长期增长。
房地产转型本身也蕴含新机会。 “三大工程”(保障房、城中村改造、平急两用设施)每年可直接拉动近2万亿投资,并带动绿色建材、智能家居等产业。 房企从开发商转向服务商,代建、REITs、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空间广阔,全国1.4亿套住宅需适老化改造,智能家居市场规模预计2029年达1.09万亿。
更深刻的变革在于居民财富配置逻辑转变。 中国家庭“重房产轻股票”的资产结构正在打破,超过162万亿居民储蓄和30万亿银行理财资金寻求新出路。 资本市场改革深化后,股市成为科技创新企业的输血通道,资金从房地产溢出,投向AI芯片、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领域。

房价走势呈现剧烈分化。 核心城市因人口流入和产业支撑,房价有底。但三四线城市人口外流,土地财政崩解,资产缩水难逆转。 这意味着,普通人买房逻辑彻底改变:靠近城市核心、房龄够新成为硬标准,老城区旧房贬值风险加大。
对个人而言,新经济方向藏着巨大机遇。 科技创新领域如AI芯片、新能源企业大量招人。医疗养老、文旅教育成为用工大户。城市更新、新基建需要技能人才。 产业升级、新基建、消费扩容等五大赛道,每个都是数万亿级市场。
但转型伴随阵痛。 税收增长16.7倍、社保增长28.7倍、土地出让金增长64倍,体制成本增速远超工资涨幅,企业不堪重负。 简政放权、国有资产划拨社保、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等改革,正是为企业“松绑”。
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的“心脏”,但如今血液(资金)能否顺畅流向新器官(科技、消费、服务),取决于血管(政策与市场机制)是否通畅。 当上海高端楼盘逆势上涨而普通二手房“以价换量”,当年轻人从追逐房贷转向为体验消费买单。这些裂痕中,新的经济逻辑正在拷问旧体系:如果存款数字的攀升无法换来生活质量的提升,那么增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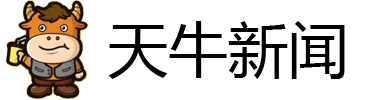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



